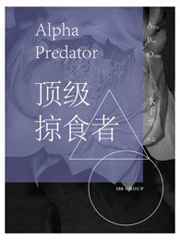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个故事 我们逃向南方(2/3)
着根长矛盘腿而坐的士兵破口骂了起来:“快滚快滚,当老子是开店的吗?没水!”那名士兵头戴着一顶尖刺盔,皮革甲上缀着圆铜钉,看着是名什长的样子。
他态度粗暴,我们心中却一起喊了声“侥幸”,勒马就要后退。
但那名看着面目和善的尉官却懒洋洋地抬起一只手,道:“且慢。
” 他这一声不大,却如一道雷落到我们心上。
马儿僵在了原地。
斗篷不安地抖动。
那军官从火堆里抓了根着火的木柴,探到我们面前歪着头打量,文士和那女孩都埋下头,躲在我们身后,不敢发出半点声息。
向慕览驱马踏前了半步,他身形高大,往前一走,就把那尉官的视野挡住了大半。
那名尉官嘿嘿一笑,抬头望着向慕览,喝道:“大半夜的,行的什么镖?全给我抓起来。
” 身边那些黑环甲士兵应了一声,挺着长枪就围了上来,我们心中大惊,全都将手摸到腰间,却见向慕览一翻斗篷兜帽,沉声道:“崔虮子,别来无恙啊。
” 那名尉官明显一愣,挥手止住手下,举起火把来凑到向慕览鼻子前看了又看,突然哈哈大笑:“这不是向游击吗?” 向慕览冷哼一声,算是回答。
崔虮子也不计较向慕览的冷淡,自顾自贴上一张笑脸,“自从莽浮林一别,有好多年了吧?一向听说你在老风子那边发财,可后来却被踢出军营,听说是手软了,杀不动人了。
至于吗,老向,就为了个女人……” “崔虮子,你比十二年前还要啰唆了,”向慕览打断了他的话,“没有想到,你居然能混进御林黑翼军,高升了呀。
” 崔虮子哈哈大笑,说:“托福托福。
”提起左手在头盔边上轻磕,竟然发出当当的金铁撞击之声。
火光下,我们看得清楚,崔虮子的左臂前端黑黝黝地闪着寒光,竟然也是一枚铁钩。
大伙儿不由把目光转向向慕览左手的铁钩,发现它们的形制大小如出一辙。
我们想到他先前讲过的莽浮林故事,心中都是一紧,仿佛脚下裂开一道火山。
这名御林军官竟然是向慕览过去的匪副,这次相遇,也不知是福是祸。
雪花从天上飘落,越来越绵密的样子,开始积蓄在我们的肩膀上。
崔虮子嘿嘿一笑,继续用铁钩轻敲自己的头盔。
他说:“老向,你前二十年抢富人,后二十年替富人卖命,这世界不是颠倒过来了么?我过去是个强盗,如今当个黑翼校尉玩玩,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吧?向将军这急匆匆的是要上哪儿啊?” “杉右,”向慕览沉着道,“汤子绪大人有一封急信,要送到他儿子处。
”汤子绪家业颇大,在茶钥是数一数二的豪门,一个儿子在屯兵堡为驻将,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
崔虮子哦了一声,沉吟片刻,又嘿嘿一笑,“向头儿的事嘛,好说好说,兄弟们,撤开口子。
” 拿着长枪猬集而上的士兵听他号令,呼啦啦地向外散开。
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将手从腰间移开,刚想要纵马离开,崔虮子却突然一扬手,将火把往我们马群中一扔,柴火上的火舌被风撩得呼呼作响,火星飞射,正中郡主坐骑的鼻子,那马骤然受惊,跳了起来,女孩忍不住“啊”地叫了一声,清脆的女声刺破夜空。
周围不论是我们还是那些兵丁全都吃了一惊,一起朝她看去。
石子落入了水中,羊羔落入了狼群。
那名什长手快,一把捞住马缰,将郡主的马拖住。
崔虮子哈哈大笑,“好啊,向头儿,我崔虮子的一场富贵,就着落在你身上了。
” 眼见事态紧急,向慕览突然跳下马去,抱拳道:“崔大人,借一步说话。
” “我为什么要借这一步给你,给我个理由。
”崔虮子乜斜着眼道。
他手下士兵已经将我们紧紧围住,长枪尖明晃晃地对着我们的脸。
我们在马上团团而转,用剑磕开枪尖,对他们怒目而视。
虽不打算束手就擒,可我们心里都明白,光在客栈前就有二十名士兵,人数是我们的四倍,要想冲杀出去并不那么容易。
向慕览哼了一声,“我救过你。
” 崔虮子笑嘻嘻地说:“谁说不是呢?可这不够。
”他左手钩子摆了摆,那些兵跃跃欲试,要冲上前。
我位置正好在向头儿身边,突然看见这个永远没有表情的人唇边闪过一丝淡淡波纹,可以算是微笑。
我暗自想,他了解自己过去的副手,知道要什么样的手段才能打动他。
果然,向慕览道:“我也知道将这女孩子送往官府,转眼就有三千金铢落袋,崔虮子,你以为我为什么还要千里迢迢,带她向北边走呢?” 崔虮子目光闪烁,不由得往前走了一步,摸着下巴问:“是啊,为什么呢?” 向慕览倏地将腰带上的剑抽出。
崔虮子脸色一变,却见向慕览将长剑插在地上,空手上前两步道:“崔大人借一步说话。
” 尉官呵呵大笑,上前亲热地拉住向慕览的胳膊,向一边走了两步,大声道:“好啊,借一步就借一步。
”又俯低身子轻声问,“怎么,你还有更好的买主?” 向慕览微微一笑,说:“这个自然。
” “哦?”尉官扬起眉毛,一副询问的神情望向他,“如果我放了你,怎么分账?” “郡主归我,赏金归羽王!”向慕览斩钉截铁地道。
崔虮子一愣,向慕览抢前一步穿到他身侧,左手铁钩重重地敲在他想要拔剑的右手上,崔虮子痛得手一缩,向慕览右手一圈一转,已经勒上了他的脖子。
尉官还想要挣扎,向慕览左手腕上那只冰冷的铁钩压在了他的咽喉上,钩尖入肉半分,一细股血登时流了出来。
向慕览当年在风铁骑手下就是有名的铁手将军,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动作依然是快如闪电。
那些兵丁还没看清他的动作,首领已经被制。
向慕览横拖着崔虮子向自己的马走去,经过自己插在地上的长剑时,轻轻巧巧地一脚,剑飞上天空,落下来时候正好掉入他的右手。
他继续勒住崔虮子的脖子,环顾四周,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宛如一块坚冰,既不紧张,也不愤怒,“让他们全都闪开了。
” 郡主想要趁机从什长手中夺回马缰,那名什长兀自不舍得放手。
我看见怒气从女孩的眉毛底下升起。
她和向慕览一样,并不永远都是冰冷的石像。
她唰地一鞭抽在马屁股上,愤怒的马儿跳入半空,几乎将那什长拖倒。
那个鬼祟的家伙只得慌忙放手,狼狈地滚到一旁。
向慕览大步跨向坐骑,却突然有人拉住他的裤脚,他低头看到火边躺着的那名垂死的伙计,正一手捂住鲜血淋漓的肚子,另一手揪住他的裤脚,有气无力地说:“求……你,救命。
” 这个伙计我们不是很熟,只记得一脸的雀斑。
落下来的雪已经半盖住他的身子,也把他肚子上的可怕伤口遮盖住了,此刻他的眼睛透出了强烈的活下去的欲望。
向慕览眉心皱了起来。
他抬头看了看天色,再看了看四周那些兵丁敌视的目光和慌乱晃动的兵刃,犹豫了一下。
他拖着崔虮子的脚步停顿了一下,向这边叫道:“颜途,看看他的伤势。
” 颜途难以察觉地皱了皱眉,跳下马来,快速检查了一下那名伙计,说:“不行了。
”他朝向慕览望来,点了点头,抽出一把短匕首,下手飞快,横拉开了那伙计的咽喉,转身又跳上马去,动作干净利索,毫不拖泥带水,正是佣兵典范。
崔虮子在向慕览的手中一边挣扎,一边大笑,“向慕览,我过去佩服你杀人不眨眼,好汉一条,可现在你婆婆妈妈的,我还怕你什么?” 向慕览勒住他的右手紧了一紧,警告道:“别废话。
” 尉官兀自嘴硬:“我为什么不能说话?十二年前,我们都是匪,你说啥就是啥;现在我是堂堂驾前御林军黑翼校尉,你挟持军官,纵跑反犯,向慕览,你果然是匪性不改啊……” 向慕览冷哼,不再搭理他,像持盾牌一样推着他向我们靠过来。
围着我们的兵丁们都有些迷惑和不知所措,他们一步步地后退,乱哄哄地闪开个缺口。
颜途拖着向慕览的黑马掉转马头,向慕览刚想将抓到的尉官扔上马鞍,突然路旁草丛一动,仿佛是风把蒿草的那些白冠吹动了。
颜途大叫一声“小心”,黑暗中一箭射出,正中向慕览的肩膀。
那崔虮子口中说个不停,却仿佛一直在等这一时刻,他使劲一挣,翻过马背向外滚去,口中狂喝:“杀了他们!” 向慕览左手横转,铁钩撕开了崔虮子半边肩膀,鲜血随着断了的甲带四散喷涌,但终究还是让他滚入到黑暗中。
向慕览还想追赶,更多的长箭却嗖嗖飞来。
崔虮子已经隐入黑暗,只听到他的声音还在扯在空中:“姓向的,我会抓住你们的。
到时候,老子当着你的面,先xx后xx,然后提着她的头去领赏……” 我们没有发现埋伏在客栈外的弓箭手,骤然吃了大亏,此刻不但要提防乱箭飞来,还要对付眼前那些长矛兵,登时势如燎眉。
羽人矛,长有十尺,矛柄用槿树干制成,平滑粗重,矛尖又细又尖,仿佛蛇牙一样闪闪发亮。
我们自己对它也熟悉异常,二十七年,我们就是用这样的长矛让蛮族骑兵吃了大亏。
此刻二十根羽人矛正如刺猬一样聚集,并排要将我们围在中间。
事出紧急,也只有六年来的战阵经验救得了我们。
只听当啷啷一声响,我们几个人在同一时刻拔出剑来,站好了位置。
向慕览也顾不上拔肩膀上的箭,咬牙跳上马背。
柳吉一马当先,罗氏兄弟殿后,我们将郡主和仓佝夹在中间,齐声大喝了一声,并肩朝外猛冲。
几支细长的长矛在脸前一晃,长剑斜劈,断了的枪杆飞在半空中,坐马铁蹄闪亮,两条前腿向前乱踢,如同一排浪狠狠地撞在黑色长堤上,我自己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眼前骤然一空,已经冲了出去。
这时候哪敢向后看,只是猛踢马肚子。
背后的马蹄声跟了上来,潮水一样响亮。
风卷飞雪中,罗氏兄弟伏在马鞍上,朝后放起连珠箭来。
芦苇丛中传出惨叫,飞出来的箭略稀了一些,我们策马狂奔,听到后面叫骂声渐渐变小消失,一声嘹亮的号角却骤然响起。
那是羽人警示敌情的号声,急促嘹亮,撕开夜空远远传开。
黎明前是最黑的一刻,我们没跑多远,一头撞进了这片浓黑之中,几乎连马鼻子也看不见了。
我拉紧缰绳,放缓脚步,回头看了一眼,竟然只有郡主跟了上来。
她的兜帽被风吹落,坐在马鞍上,身子微微颤抖。
我见她一张小脸跑得通红,紧咬着牙齿,又害怕又痛苦的样子,一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对她说:“别担心,不管出了什么事,我……我们一定会护送你到冠云堡的。
” 她抬起脸来看了我一眼,那双眸子黑白分明,“你,以为我会感激你吗?”她直望着我的眼睛说,然后把头别了开去。
那就像平静的绸缎上突然隆起的一条皱褶、一道裂缝。
我悚然而惊,但那是她和我说的惟一一句话,此后她就不说了。
蹄声又逐渐响亮,这次是伙计们跟了上来。
颜途下巴上糊满了血,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朝我嚷道:“妈的,停在这儿干啥?”错马而过的时候,照我和郡主的马屁股上各抽了一鞭子。
我们直跑出了二十里地,直到再也看不见路,担心马在黑天里摔进坑里,这才停下来查点损失。
颜途下巴上的血不是他的,但臀部中了一箭,幸喜没有大碍。
问题是,向慕览不见了。
罗鸿一边用白布给颜途包扎伤口一边说:“我好像看见他的马中了两箭,怕是跟不上来,落在后面了。
” 我们等了又等,草丛里传来的每一声响动都让我们既紧张又期待,既希望那是向慕览回来了,又担心被官兵追上。
但那只是一只窜过的黄鼠狼,或是一只迷路的沙鸥,向慕览则始终没能跟上来。
仓佝一手扶鞍,另一手拖着郡主的马缰,声音颤抖地说:“不能管他了,我们得自己走。
” 这家伙颤抖的话音能传染恐惧,我在夜色飞雪里望向一个个弟兄们。
漆黑的夜里,只看得见他们白石子一样的脸。
罗耷一抹头,大声喝骂出来:“去你娘的,我们怎么能扔下自己人?” 其他人却像石头一样沉默着。
“喂,你们怎么说?说话呀。
”罗耷拉着马团团乱转。
末了颜途说:“不会只有一队巡逻兵,警号已经发出,我们停留在此确实危险。
” “难道扔下头儿不管?”罗耷求助似的转头看着边上,“哥,你说呢?” 罗鸿“嗯”了一声,低下头去却不开口。
“这么暗的天到哪儿找他?”颜途说,“可要等到天亮,我们就会有更大的麻烦。
”他话音里带着不多见的焦躁,大伙儿知道他说的是实话。
颜途可不是个怕死的人,怕死的佣兵活不长久。
我们都不怕死,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恐惧。
过去的生活让我们学会怎么去掩盖这层恐惧,有些人用他的忧郁,比如罗鸿;有些人用大声的笑,比如罗耷;有些人用沉默,比如柳吉;还有些人用冰冷的盔甲包裹自己,比如……郡主。
我们中间,还有谁是这样的呢,还有哪些外面表现只是伪装呢? 我的伙伴们在团团乱转,他们着急,恐惧,但是拿不定主意。
这是任何行动的最大忌讳。
我很想说,我们一定要把这姑娘送到冠云堡,但那一句话我就是说不出来。
我是个拙于言行的人,向来只是听命行事。
向慕览不见了,这让我六神无主。
没有了向慕览,我们怎么可能把女孩送到地方呢? 罗耷还在焦躁地兜着他的马,“难道要为了这妞儿,丢了我们头儿?” “老二,你冷静点。
”罗鸿劝道。
阿吉一声不吭,突然扭转头,催马向夜色中跑回去。
他这人木讷寡言,平日里话不多,却是个倔脾气。
罗耷愤怒地叫道:“你去哪?” “等我半个时辰。
”阿吉喑哑的声音从夜色里传出,一瞬间之后就掉落在草丛里,听不见了。
罗耷犹豫片刻,似乎想跟上去,但稍一犹豫,就丢掉了阿吉的背影。
我稍稍侧头,看了看那女孩羽毛一样光洁明亮的脸。
她无动于衷地低垂着头。
我对柳吉的单独行动有点生气,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拨马而去,却不给我任何提示或讯息。
他不需要我。
是的,在离开之前,阿吉他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似乎是觉得我帮不上他的忙。
我把这怒火强转向了自己,也许,我确实帮不上忙。
我们等啊等啊,等到天色逐渐明亮,慢慢看清黄色的枯草上压着的白雪,看清了对面人脸上的焦躁神情,罗耷牵着他的马来回转着圈,几乎将地上的草踏成一圈平地。
我绝望地想,阿吉再也回不来了。
“我早说了,他一个人不行。
天要亮了,”仓佝连连催促,“快走,快走。
” 看我们都不肯继续前进的模样,他就破口骂了起来,从颜途开始,一路点名骂下来,骂的都是青都官话,我们听不太懂,罗耷却不耐烦起来,用长剑指着他吼道:“你他妈那张嘴里再喷一句废话,老子就切了你的狗头拿去喂乌鸦!”他剑上的血甩到了仓佝脸上,仓佝脸色铁青,虽然气得浑身颤抖,却果然住嘴不再吭声。
清晨的时候,雪停了一会儿。
我们看见白色的几乎没有热量的太阳慢慢地在空中移动,罗鸿突然轻轻地吹了声口哨,示意我们注意地平线上一道隐约移动的黑线。
“巡逻队。
”他轻声说,“样子有几百人。
” 我们身周的矮灌木很高,正好能遮蔽住马和人,但被远处的巡逻队发现只是早晚的事。
颜途点了点头,轻声说:“没法等了,我们走吧。
” “等一等。
”一直不说不动的郡主却突然开口了。
我们一愣神的时候,就听到了隐约的马蹄声,单薄而绵密。
一转眼间,两个骑者的影子踏着晨光向我们跑来。
柳吉不但把向慕览带了回来,还找回了他的马。
迎上前去的人当中,就数罗耷的嗓门最大,他猛烈地捶着柳吉的胸膛,似乎是愧疚自己没跟上去。
阿吉朝我转过头来的时候,我没有报以往常的会心一笑。
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恨他。
突围的时候,向慕览的腿弯被一根长枪刺穿了,跑出几里地后体力不支,滚下马去,在草丛里伏了半天,直到天大亮后才被柳吉找到。
阿吉牵着向慕览的马,向慕览侧躺在马鞍上,用斗篷裹着腿,小心地不让血滴到地面或是枯草上,所幸伤势不重,向慕览体格健壮,支撑得住。
颜途替他处理伤口,脸色赧然,有点内疚的模样。
向慕览倒是坦然,对大家说:“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听颜途的,不要回头救人。
” 不能为了一个人把更多的人搭上,这是佣兵的守则。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若是换了个人掉队,向慕览可能会抿着铁线般的嘴唇,冷冷地道一声“走”,讨论的机会都不留给大伙。
他为人死板,冷酷无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愿意为他卖命。
佣兵还有其他的守则,非常多,每违反一条都是罪过,但无论哪一条守则都紧紧地围绕一个核心:完成主顾的使命。
信誉如铁,信誉就是我们的性命。
这就是黑水誓约。
它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
血止住了,只是伤口周围有点发黑,向慕览皱着眉头,将重心压在伤腿上试了试,“还能骑马。
”他叹了口气,“妈的,你们说,我老了么?” “当然没有。
向头儿怎么会老呢?”颜途打了个哈哈。
“如果不是老了,我那一下怎么会让崔虮子跑掉。
”向慕览问,语气里带上了点怒气。
颜途耸了耸肩膀,不知道他是对谁生气。
我们不敢接口。
向慕览一贯是我们眼中铁骨铮铮的硬汉子,天塌下来也不会弯一弯眉毛,哪知道也会露出这样的萧瑟之意呢。
崔虮子说他心变软了,杀不了人了,是真的吗?可是不够冷血,佣兵又怎么能活下去呢? 颜途摆了摆下巴,指着远处那条散兵线,问:“朝东朝南的路都被封住了。
向头儿,现在该怎么办?” 向慕览将头垂到胸膛上,似乎极疲惫的样子,沉默良久才说:“不能走凄凉道了,我们得直接穿过南药,从莽浮林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官兵。
” 颜途的脸色变白了,“南药……可是,有瘟疫……怎么办?” 罗耷也嚷道:“碰到官兵我们还知道怎么对付,大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可这瘟疫来去无踪,即便想对付,也使不上劲啊。
” 向慕览抬起头来,浅白色的眸子盯着大伙儿看,“那么还有别的路吗?”他看到谁,谁就低下头去。
向慕览摆了摆头,“请郡主上马。
” 马背上一动不动的郡主突然再次开了口,“那就别送我走了。
” “什么?”大家谁也没听清。
“别管我了,你们自己走吧。
” “郡主……”仓佝震惊和惶急之情滥于言表。
向慕览看看她,平静地说:“我不是为了你。
”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我,你是为了还债,还自己的债!”女孩彻底爆发了,她挑衅似的转过头来看其他人,鞭子在她手里被捏得变了形,“而你们,你们是为了钱,为了女人,为了你们佣兵团的名誉。
” 她那小小的鼻翼变得通红,呼吸急促,“有谁是为了我?有谁是为了我冒死向前的呢?你们有吗,有吗?”她的话好像阵阵鼓声落入我们被霜冻坏了的胸膛里。
“没有,没有,没有!”她喊叫道,声音越来越低,最后一句话和着泪水一起落了下来,“别在这里充好人了。
我希望你们全都死掉,死掉!” 仓佝上去拉她,却被她一鞭子抽到了脸上,“滚!滚开!” “请郡主上马。
”向慕览又喝了一声,声音里充满了怒气和不可违抗的威严。
他一个人率先向前走去,我们只看见那孤独的脊背在苍黄的大地上投下一道影子,斜斜地指向北方。
“跟上来。
”他喝道,依然不带一丝感情。
越过八盘岭,漫山看去都是荆棘密布的红剌树和雪松,颜色深黛,长枪军阵一样密密地挤立在一起,树梢尖漂浮着一层层灰色的雾气。
这说明我们已经离开了维玉森林,开始进入莽浮林了。
莽浮森林地形错综复杂,地势破碎,外来人极容易在此迷路,也只有在这里当过山贼的向慕览对道路极熟,我们自然都听他的。
从开始动身起,向慕览就一路催促,赶着我们前行。
我们走的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狩猎小径和干溪谷,路有时和蛇一样的歧路交杂缠绕,有时埋没在荒草灌木里,走上一两里地才又复现。
虽然道路如此偏僻荒凉,走起来又艰难,向慕览却不准我们休息,他说:“那边可是有一个人,对这儿的路和我一样熟,谁知道他们能不能追上来。
只有快马加鞭,尽量多赶点路,才可能甩开他。
” “这边有瘟疫,他还真能追进来不成。
”颜途回头说话,一不小心被一根横在路中间的树枝抽在脸上,几乎把他挂下马来,气得他破口大骂。
“十二年前,他一定会追过来,但现在就难说了,人总是会变的。
”向慕览说,左右看了看,低头钻入被一丛矮栗树完全挡住的小路里。
这些乱麻般的小路有时也会穿过些田舍空地,虽然早听说疫情严重,我们却从来没想到过会是如此情形,简直是触目惊心。
田野间空旷无人,屋舍倒塌,稻田里成片熟透了的粮食倒伏在地里腐烂,却静悄悄的看不见农夫劳作,也没有牲畜的动静。
就连向慕览也承认,一个变沉寂了的莽浮林与过去大不相同。
我们被林间的静默所感染,日渐寡言。
为了防瘴毒,我们嘴里含了药草,以白布蒙面,连马口也罩住,柳吉稍通明月祝福术,这时也为大家祈念。
每日清晨起来,颜途就会神情吝啬地洒一点酒在柳吉手上,我们眼看着一道微微白光在他掌心泛动起来。
他以这只手依次摸我们的额头祈福,淡淡的酒香透入鼻子,倒是让人精神一振。
不过面对沉寂的山林和呼啸的风,这酒的淡香就显得微不足道毫无用处。
仓佝更是轻蔑地拒绝了柳吉的术法祈福:“你那是江湖术士的下等伎俩,别用奴才的粗手碰着了我们。
喂,要摸,就摸我们的马吧。
” 我们听到他的话都是愤愤不平,但柳吉性情好,只是摇摇头,然后低首退开。
某一天开始,我们在路边发现了新挖的坟墓。
起初每遇到了还会觉得不舒服,后来见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看到坟墓,总比看到活人好。
”颜途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灌了一大口酒。
这一日的路程更加艰难,厉风夹杂着冻雨迎面而来,道路上除了烂泥就是坑。
路边偶尔还能见到死牛死马、牲畜动物,一些黑乌鸦在死尸堆中欢声大叫,跳跃啄食,如同过节一般。
腐臭的气息伴随一路,躲都躲不掉。
落雪时有时无,地面的雪积不起来,幸而如此我们才留不下脚印。
进入南药地界,我们改为白日行军,但并未让我们觉得轻松一些。
我们不但拐着弯走,倒着走,还经常踏入结冰的小溪里,顺流或逆流走上三四里地再上岸前进,一切都是为了甩掉跟踪。
勾弋山那明亮的山脉影子原先始终在我们左方晃动,现在则变得忽左忽右,忽前忽后。
向慕览也要时常爬到某棵大树上,才能辨清方向。
我们行路更加小心,有人驱前侦察,有人殿后警戒,宿营时双人站岗守卫。
其实守卫的用处不大,因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所有人都会从梦里跳起,抓紧手中的武器。
向慕览总是尽量让我们多走一点路,他头上罩着一片乌云,像他的大黑斗篷那么黑,他还不停地向后张望,我们这样骑惯马的角色都浑身骨头酸疼。
我们自然都想起了那个古老的说法:羽人也许更应该在密林的树上穿行,而不是骑马。
而向慕览对我们受的一切苦都无动于衷。
“多走点路总比动刀子强,”他说,“继续前进。
”直到天色黑得有摔死人的危险才让我们下马扎营。
有一天一早起来,我们就觉得天气格外的冷,风也有些不对劲。
颜途把拇指舔湿,伸到空中,然后沮丧地说:“是西北风。
” 风已经换了方向,它径直地从西北方吹来,吹开哗啦啦响的树叶,穿透了层层厚斗篷和毛衣。
即便套着厚厚的羊皮手套,手依然僵硬得拉不动马缰。
“知道吗?西北来的风叫厉风,老羽人说西北风是瘟疫之风。
”罗鸿一边拨开挡在前面的树枝一边嘀咕。
“那又怎么样?”罗耷没精打采地缩了缩脖子,“老羽人有没说过大冬天的不该出门?” “你们两个!老羽人说走路的时候少说话!”颜途恨恨地瞪了他俩一眼。
那一天我们在小山丘上的林子中安了营地,罗鸿到丘下打了水来,向慕览闻了闻水,就说:“这水有问题。
” 我们向上游走了几百步,果然看到在芦苇丛里躺卧一具尸体,四肢扭曲,全身浮肿,溪水寒冷彻骨,上面漂着块块浮冰。
死人蓝绿色的脸浸在水里,被一群小鱼啄没了眼睛。
我们死人看得多了,但如此让人胆战心惊的尸体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们站得远远的,不敢再碰那水,也不敢停留,又往上游走了七八里地,才再停下来宿营。
我们吃的是自己带来的干肉,水也一定烧开了再喝。
姓仓的那个御史更是小心翼翼,也许是嫌我们身上太脏,他根本就不让我们碰任何可能被郡主用到的东西,自己满头大汗地卸鞍上鞍,拉绳子搭帐篷。
我们乐得省事。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没发现一点有人跟踪的痕迹。
风又实在凛冽,向慕览这才松了口,那天晚上允许我们点火取暖。
佣兵的简易帐篷通常是找三棵品字形的大树,绷上两根绳子,挂上厚帆布,让帆布的三边垂到地面,就是晚上睡觉的地方了。
指望它有多挡风是不现实的,但聊胜于无。
对颜途来说,最难受的就是找不到酒,虽然看护严密,他的宝贝酒囊还是越来越空,他的脸色也就一点点难看下去。
晚上我们轮番守夜,挤在火边烤干湿斗篷,反正不会碰到活人,柳吉就又开始吹他的笛子,这家伙就是不喜欢说话。
我们说,他把自己的话都扔进笛子里去了。
他有一根很不错的笛子,质料坚实,竹子的颜色里透着红,音色清亮。
这庄稼汉有这样的好东西真是不配。
这一次也许是看多了死人,他的曲子里尽带上凄苦的味道。
我们跑了一天路,在荒郊野外吹着风,受着冻,再听他这怨曲悲调,忍不住都抱怨起来,连好脾气的颜途都说:“阿吉,再吹那鬼调子就把你的头剁下来!来个欢快的……来个《二姑娘》吧。
” 二姑娘是首院子里流传的艳曲儿,人人都会。
颜途一提议,没等柳吉答应,大家儿已经一起吼了起来: 对面路上走来个谁, 就是那要命的二姑娘, 头上插花回娘家, 走到叶黄儿松松树林旁, 树窠里跳出个小杂种, 扯住手儿不放松。
这下流调子和阿吉的曲调混杂在一起,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阿吉憨厚地笑笑,将笛子收了起来,听我们瞎唱。
隔十来步远,郡主那边的火堆则始终寂然无声。
向慕览走过来看看,侧头听听附近的动静,然后又大步走远。
自从遇到崔虮子后,他总带上点狐疑的神色。
我们都有些为他担心。
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把头从帐篷里探了出来,眼望天空,期盼星星能够出来。
但我没有等到。
半夜里风夹杂着雪,铺天盖地而来,压垮了火堆,我们挂在火边刚烤干一点儿的斗篷又全都湿透了。
好不容易熬到清晨,我们从雪堆里挣扎出来,看见仓佝正围绕着他们那边两顶小小帐篷忙碌,每次端茶奉水前都要先正衣冠,拍打着想象中的灰尘,然后跪在地上双手送入帐篷内。
这些贵族即便在野外,也是礼数多得要命。
罗耷狞笑着说:“我很想知道,这些贵族会不会比较皮厚所以不怕冻?” 脸色发青的仓佝一边吸着鼻涕一边走了过来,冻得说话都不太利索了:“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不能一直往前赶路了,”向慕览系紧自己的马肚带,然后宣布,“我们得找些给养。
” 我们的给养确实消耗得太厉害,驮马原先满驮着干鱼、牛肉、青豆和面饼,现在已经几乎空了。
“说什么我们也得搞点酒来。
”颜途嘀咕着说。
中午时分我们靠近了一个村子。
说起来那村子实在算不上村子,只有四五栋树屋零散地围绕着一棵高大畸形的树木,铺着石瓦和草皮的屋顶已经漏了。
那棵畸形的树有着暗红色的叶子,苍白的枝干斜斜扩张出去,遮蔽了半个村子。
“有情况就退后。
尽量别接近任何人。
”在村子前驻足时连向慕览也有些犹疑,但他的告诫多余了,村落里和森林里一样空荡荡的。
夹带着湿雨的风穿过空荡荡的村子,破窗户开开合合。
颜途拔出剑来,轻巧地从马背跳上树干,罗鸿兄弟弯弓搭箭,在下面警戒。
“别指望什么了,全是空的。
”颜途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剑垂在手里。
我们开始两人一组,快速搜索了每间屋子,像当年偷袭蛮人营地时做的那样,可那时,毕竟我们面对的敌人是有形的。
这一次呢?我抓着剑闷想,敌人会是看得见的吗? 屋子全是空的,连家具都没剩下几件。
空气里有一股腐败的气味。
颜途倒是发现了一个酒瓮,打开盖子,里头却跳出只老鼠,唬了他一大跳。
可是就连活老鼠我们也难得一见。
村口会合时,大家都面色沉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虽然日头正当午,这村子却给人一种凉飕飕的感觉。
“走吧,到下个村子去碰碰运气。
”向慕览阴沉着脸说。
大家跳上马背,颜途回头看了一眼,这儿太阴冷太静默了。
也许是为了躲避这种令人不快的沉寂,颜途不自觉地又哼起了那首《二姑娘》: 对面路上走来个谁, 就是那要命的二姑娘, 樱桃好吃树难栽, 哥哥我有那些心思口难开。
这单调的歌声在无人的村子里回荡,听起来倒像是鬼哭。
“不对,”颜途突然住了口,一皱眉头,“你们听。
” 我们凝神细听,竟然听到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咸鱼少爷穿成反派的白月光糖三甲
- 纪律准则顾言
- 老婆他又乖又娇柒神
- 涟漪效应时星草
- 重姒(双重生)雕弦暮偶
- 惶惶小霄
- 神级工业主五彩贝壳
- 请不要给工具人加戏[快穿]洛云九
- 横刀城郭如旧
- 玄学,最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心理学最凶辅助
- 异世之王者无双蓝领笑笑生
- 管家总被人觊觎[快穿]豆腐军团
- 嘘,别闹倾唐
- 我是极品炉鼎正月初四
- 成为恶毒女配后我拐走反派发如青丝
- 漫画Bking自救指南千秋岁引发
- 娇弱贵妃精神稳定叙华
- 陛下替我来宅斗杯雪
- 不要打扰我飞升昭文
- 阴阳渡梦溪石
- 武侠之神级捕快紫衣居士
- 当上帝重新开始进化十二翼黑暗炽天使
- 溺渊池总渣
- 别那么野顾子行
- 汹潮林汀汀汀汀汀
- 怪物都是恋爱脑山有青木
- 禁止和高危物种谈恋爱![快穿]柿宴甜
- 轧戏祖乐
- 狩心游戏碉堡堡
- 坏春天何缱绻
- 随军年代文二代躺平日常[六零]最近爱吃酸辣粉
- 炮灰夫妇今天也想暴富臣音
- 师姐空有无边美貌赏饭罚饿
- 男花魁只想攒钱买地(穿书)螺髻山下客
- 有钱算特长吗八月糯米糍
- 漂亮O被直男室友盯上后木旦旦
- 陛下今天火葬场了吗/无情眼杳杳云瑟
- 传说中那一位传说舍山取草
- 天才制卡师龙柒
- 穿到年代文里当建筑师葡萄干颂
- 被迫奉子成婚之后云闲风轻
- 春天禁止入内yespear
- 闻妻有两意忘还生
- 医者仁心,我,全球大外科第一人君子兰3月
- 世界名画老天鹅啊
- 血税大瓜熊
- 雨意荒唐[先婚后爱]州府小十三
- 完蛋!我成替身了!六月观主
- 娇弱贵妃精神稳定叙华
- 从西周建立千年世家花非花月夜
- 夏日撞上南墙甜舔
- 望长天/仙子,请听我解释弥天大厦
- 壮汉老实受被豪门大佬独宠了木万千
- 禁止和高危物种谈恋爱![快穿]柿宴甜
- 回声[无限]冻感超人
- 五零香江豪门生存法则老衲吃素
- 毛茸茸过敏,但能rua精神体初啾
- 21号信箱/湿吻逢春朝
- 悬鸟娜可露露
- 娘娘福星高照[清穿]岳月
- 清末的法师黄文才
- 成为龙傲天的大老婆[快穿]椒菌
- 在异世大陆讲华夏神话不吃猪肉吃鱼肉
- 黑月光她只想夺权元余
- 异世海商魔法少女兔英俊
- 以山神之名,敕令天下万物!八个肾的男人
- 都说了这是狙[综英美]殷忆华
- 我家垃圾山上全是宝莫然如风
- 传说中那一位传说舍山取草
- 和死对头成亲后小鱼卷
- 血税大瓜熊
- 一个雨天殊娓
- 前男友成为首富后乌龙煮雪
- 伊尔塔特的农场秋野姜
- 从西周建立千年世家花非花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