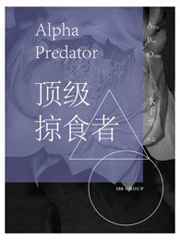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五个故事 我们逃向南方(3/3)
风中隐隐有微弱的呼喊声。
“救人,救人。
” 我们仔细寻去,发现一丛衰草遮蔽下竟然有口枯井,井挨着路边,口子又小又圆,黑黝黝的看不见底。
如果不是细心查找,我们中没准有人会掉进去。
呼救声正是从下面传出的。
“谁在下面?”罗耷喝问了一声。
声音停顿了一下,然后变得更大声更清晰:“救命救命,我是人啊,救救我吧。
” 向慕览点了点头,罗耷从马背上解下粗索,利索地编了个绳圈扔了下去,朝下面喊:“把圈套在腰上,绑好了就抖两下。
” 绳子在井口抖抖索索动了一会儿,不动了,然后又抖了两下。
我们将粗索捆在马鞍上,一步步驱马后退,将井里人拖了上来。
那人把双手挡在头上,遮蔽刺目的阳光。
皮帽子边缘露出一头枯黄色的头发,淡蓝色的眸子下突兀出一只鹰钩鼻子,头发梳成小辫,看上去好像一辈子没洗过,就连胡子也分梳成几绺辫子的形状,身上套着件狼皮大衣,狼毛反露在外,背上还背了个破布包。
他饿得两眼发青,见了我们依旧还能龇着牙笑,笑得也像条狼。
“来口酒喝。
”他要求说。
我们骑在马上,好像一堵半圆形的墙环绕着他,个个冷笑。
“嘿嘿,是个蛮人。
” “蛮人。
” “怎么,来抢劫时没注意脚下?” “这小子敢吗?我看更像个小偷。
” 蛮羽战争虽然结束了,羽人和蛮人之间的仇恨可没结束。
我们围绕着他嘲笑,不留任何情面。
井中人就像条迷失道路的小狼,被群犬围着逼入死角。
这样做虽然不英雄,但我们只是佣兵,不是英雄。
蛮人舔舔嘴唇,用哀怜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不是小偷。
大人们,饶命吧。
” “村里人呢?” “给我点酒。
三天,就啃了点雪,井底的,快要渴死了。
” “给他。
”向慕览说。
颜途满脸不快地摇了摇酒囊,嘟囔着扔了过去。
一路上无处补充,他的酒已经所剩无几了。
那人急不可耐地把囊口塞进嘴里,一些酒顺着肮脏的胡须流到了他的前襟。
喝了酒,他的眸子变得鲜活了一点,面孔也有了活力,“再给点吃的。
”他要求说。
颜途一鞭子抽到了他肩膀上,“我在问你,村里人呢?” “没有人了吗?我下去之前他们还在呢,”那蛮族汉子耸了耸肩膀,话变得连贯起来,“兴许村里死了人,都吓跑了吧。
” 向慕览的马不安地动了一下蹄子,“死了人?这村子里有瘟疫吗?你是怎么掉下去的?” “我可不是自己掉下去的,听说你们羽人一到晚上就看不见,跟鸡似的,哈哈。
谢天谢地,我可不是羽人。
”他站立不住,摇摇晃晃地坐到了地上,“没吃的吗,牛肉干?烧鸡?没有烧鸡来块大饼也行。
” 罗耷凶猛地往前跨了一大步,“听清楚了,我们老大不会再问第二次,像你这样的人我杀了不少!快说,你是怎么掉下去的?” 这蛮子对我们的态度算是认真了一点,半死不活地抬起头来,“我想帮他们治病人,可是没治好,他们就把我扔到这井里。
” 我们惊讶地互相看了看,然后哄笑了起来。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大夫啊。
”罗鸿讽刺地说。
“胡乱混点饭吃。
”蛮人说,拼命地赔着笑。
“这次好像没混成嘛。
”向慕览扔了块白面饼过去,蛮人狼吞虎咽,噎得直翻白眼。
稍等了一等,向慕览才问:“既然你是郎中,治得了这病吗?” 蛮人一边猛塞,一边连连摇头,“这病太古怪了,我从没遇到过如此烈性的瘟疫。
” “你还真懂得一点。
”颜途说,话里明显带着刺。
蛮人把最后一口面饼子塞进嘴里,意犹未尽地使劲舔着指头,“我和你们说,这病只要与病人面对面呆过一阵子,起初几日什么都不知道,还傻呵呵地骑马种地,没过几天就开始发热咳嗽,鼻子流血,那就是快完蛋啦。
” 颜途不安地向四处转了转头:“谁都会得上吗?” “不是,那当然不是,”蛮人愕然地眨了眨眼,他的眼睛细眯眯的,就像一条缝,“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得上,但发作了以后却几乎全死。
” 罗耷听他说得恐怖,放声笑了出来,“少他妈在这里吓唬人,你见过了病人,自己怎么不死?” “哈哈,老兄,蛮人可不容易死,”蛮人得意起来,拍着胸脯说,“我们蛮族人有万应灵药。
” “卖万应药的蛮族人可不少,”颜途冷笑一声,“这种药我在战场上见得多了,小瓷瓶装的,拿热水洗了手,涂抹全身,是吧?呸,最后谁的命也没救成。
” 蛮人尴尬地笑了笑,果然从背后的袋子里掏出一个瓷瓶来,却依然不服软,“万应药确实是谁都有,不过我这药可不一样,真不一样。
你们用的法子不对吧,用热水烫了手吗?全身都得涂啊。
” 颜途又朝他头上挥了一鞭,打得不轻也不重,“呸!什么万应灵药,那怎么还把你给治到井里去了?我看你卖药是假,趁机偷鸡摸狗是真吧。
” 蛮人嘿嘿地笑,也不分辩。
把瓷瓶收好,又伸出满是污泥的手:“再来一块饼子。
我在井底可饿坏了。
” 他头一次注意到空荡荡的原野,然后扫视了一遍后面的荒原,看到了地上的残雪,脸色登时变了,“带上我走,我在这里会饿死的。
”他要求说。
没错。
厉风已经起来了,在这么北的地方,没有食物,没有帐篷,我们不带他走的话,他一定会死在这儿。
“别管那么多了,”颜途扭头提议说,“杀了他。
”他提议得对,我们自己的给养还不足呢,带上这么个蛮人只能添麻烦。
“杀了他。
”罗耷也点了点头。
柳吉没有说话。
罗鸿啪的一声,让剑从鞘里跳了出来,而仓佝抱怨说:“快点动手,我们耽搁了不少时间了。
” 蛮子知道我们可不是说笑,他眼睛里开始灌满恐惧的神色,声音也变低变嘶哑了:“别杀我。
我什么也没做,我没偷东西,真的。
” “我没偷东西。
”他渴求地看过来,那目光简直要让我冻僵。
那些眼睛,他的眼睛,还有所有那些星星。
但我一声也没吭。
现在改变这些已经太迟了。
我们入了这行,就是要杀人的。
“不能杀。
”向慕览说。
“嗯?”我们一起把头转向了他。
“别碰他,没看出来他年纪还小吗?”他说。
那个蛮人虽然留了胡子,但额头光洁,确实还小。
“带他走?”颜途本来已经跳下马朝那蛮子走去,现在则不可思议地转头问向慕览。
罗耷也斜睨了蛮子一眼,小声嘀咕:“小又怎么了,这样的小孩,我们每个人都杀过好几十个。
” “我们没有多的马。
”颜途没好气地说。
“物资少了,正好空出了一匹驮马。
”向慕览不动声色地说。
颜途的不服气是谁都可以看出来的,他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蛮子,胳膊一甩,手上的剑插在蛮子的脚尖,飕飕地颤动。
坐在地上的蛮子吓得向后退去,但颜途那一剑贴得太近,将靴子尖刺穿才插入土中,使他后退不能。
骑在马上的向慕览呼的一声抽了一鞭子过来,将颜途的半圆盔打落在地。
“玩什么玩,”他怒喝道,“不管你想什么,这里只有我,是你们的头。
” 颜途不敢争辩,拔起剑,捡起头盔向后退下。
向慕览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余怒未歇,继续骂道:“你嫌仗还没打够是吗?那就杀过灭云关啊,到瀚州去杀蛮子啊,那里全是蛮子。
” 颜途紧闭着嘴,回到我们中间时却悄悄抱怨:“我们向头儿,还真是婆婆妈妈了。
” “这匹马,只怕一跑就要断气。
”蛮人埋怨说,但还是一跃跳上马背。
虽然我们看不起这些肮脏的罗圈腿,但不得不承认,这些矮子玩弄马匹的技术还真是令人叫绝。
仓佝红了脸和向慕览大声争吵,显然是很不高兴,但向头儿用铁和冰一般的面具把他给赶跑了。
风呼啦啦地从西北方吹来,把暗红色的叶子吹得漫天飞舞,在暮色中仿佛沾血的乌鸦。
向慕览开始不再令行禁止了,我们的队伍出现问题了。
而这件事情,我不由得缩了缩脖子,坦白说,我对这事情有种不好的预感。
厄运甚至都没给我们喘息的时间,在半夜里就猛扑了下来。
我们被一阵吵闹声惊醒,发现白天里救了的那位蛮人满脸青紫,喘不上气,剧烈咳嗽,把身子咳得如同风中抖动的树叶。
“那病来了。
”颜途说。
“全都退开。
”向慕览喝道,大跨步上前。
他从那蛮人的袋子里掏出小瓷瓶,烧上一壶热水,然后脱光了蛮子的衣服,照先前这人说的法子给他身上擦药,搓揉全身。
他忙了整整一个晚上,早上的时候,蛮人似乎平静了一点,但胸口上却出现了黑斑,随即蔓延到胸口。
“我没事,我没事。
”蛮人笑嘻嘻地说,却突然一阵剧烈咳嗽,面色变成青紫,血从鼻子里冒了出来。
他躺在地上,总是低声说:“我没事。
”向慕览给他水他也不喝,到了中午的时候,他半抬起头看看我们,最后说了一声“我没事”,然后就死了。
“呸,”向慕览说,“上了这小子的当,这法儿不行。
”随后就拼命用热水洗手。
“我们和他同走了大半天,用一个锅子吃了饭。
”颜途冷静地指出。
颜途说得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吓掉了魂。
瘟疫如此可怕,而我们却与这人同行了一天一夜。
仓佝疯狂地跳起脚来,要不是自觉不是对手,他会朝向慕览扑去。
他责备我们不该随便伸手救人,如今惹祸上身,真是百死难赎。
“我们快到冠云堡了啊,我们就快到了!”他哀号着说,“出了事我拿什么交给凛北王,我拿什么交给他?”我们这群野汉子全死光了,也不及他的郡主一根手指金贵。
“小心你的话。
”颜途说。
仓佝不予理会。
“小心你的话。
”罗耷说。
仓佝消停了一会儿。
他比较怕罗耷,也许是因为他个子高,胡子浓,面相凶。
然后颜途把向慕览拖到一边去,拖到一株高大的红松背后,本来我们听不到他们的话,但他们的语气逐渐激烈起来,说话声越来越大。
最后我们听到向慕览压着火气说:“行了。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转过身向我们这边走回来,但颜途却伸出一只手,固执地把他拦住了。
我们都倒吸一口凉气,等待我们的头儿向慕览爆发。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时刻却向后拖延了。
颜途在说话,他的话毫不客气:“不对,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弟兄们信任你,把命交到你手上,你就要为他们负责。
” “我是在负责。
你以为我只是在乎自己吗?”向慕览愤怒地挥了挥钩子,铁钩仿佛要在幽暗的林下划出火星来。
“你不是吗?”颜途又向危险线迈进了一步。
“黑水的名誉……大家都缺钱……你不为自己的下半辈子考虑吗?”向慕览奇怪地笑笑,伸出钩子似乎要拍拍颜途的肩膀。
“钱算个屁!”颜途猛拨开了向慕览伸过来的手,“我们该回头了,你心里想的只是把这姑娘送到冠云堡,别的什么都不管。
那是你的事,我们不干了。
” 这是第一次有人公开置疑向慕览的权力。
我们比向慕览更要震惊,个个目瞪口呆,而向慕览的脸黑得如同天上所有的乌云都聚集到了其上,他向后跳开一步,手抚剑柄,左手的钩子闪着寒光。
颜途则双手抱着肩膀,目光炯炯,朝向慕览回瞪过去。
向慕览的牙咬得紧紧的,刮得铁青的腮帮子向外鼓了出来。
那是他发火的表现。
曾有一名新来的佣兵不懂规矩,在他发火时上前说话,结果被向慕览一剑劈下半边耳朵。
我们都以为他会拔出剑来,和颜途一较生死——这是遇到挑战时,佣兵的唯一选择。
我们看看向慕览,又看看颜途,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帮谁。
现在的佣兵营里,老向是我们的头儿,但颜途则是我们在黑水团中的生死兄弟,事实上的头目。
向慕览身上那件抖动的斗篷却突然平静了下来。
他的嘴唇依旧抿得紧紧的如一条线,但身上的肌肉却全松弛了下来。
“这一票确实太危险,是我对不住大家。
”他说。
连颜途都愣住了,一时转不过这个弯来。
向慕览缓缓地伸手入怀,掏出一张烙着花纹的白鹿皮。
“这是祥瑞钱庄的银票,可以兑换一千金铢,此刻柜面上也就这么多了,”他说,“你带弟兄们回去吧。
把钱分了。
” “那你……”颜途不知所措地接过白鹿皮,突然有点结巴。
“荣誉就交给我吧。
”向慕览说这话的时候,挺直了腰。
他灰色的眸子里毫无感情,惟见冷峻。
颜途后退了一步。
一瞬间里,这个人又回复到我们所认识的向慕览的模样。
这样的向慕览绝不动摇、绝不妥协,也绝不容情。
我们知道自己再多说一句话,必然会面临可怕的局面。
他走过去拾起马缰,跳上马去,赶到郡主和吓得哑口无言的仓佝跟前,拉起他们的马缰,拖着他们继续向北而去。
颜途拿着那张银票发了半天愣,望着他向北的背影,然后狠狠地向地上吐了口唾液。
他转回头来瞪着我们,怒吼道:“看个屁,还不快跟上!” 我们把死人留在了树下。
他很快就会被乌鸦吃掉,而我们中会不会有人步他的后尘,按那个死人的说法,五日内就能见分晓。
罗鸿惆怅地说:“我希望自己走运点,能够最后一个倒下。
” “最后一个倒下也是倒下。
”颜途嘴里叼了根草枝,没好气地回答。
“那仍然算是走运。
” “蛮子不是说了吗,碰了病人的,未必都会得病。
” “那总会有人得病吧,谁和那个蛮子说的话最多?我们得算一算。
阿吉就除外了。
他反正从来也不说话。
” 阿吉由得罗鸿胡诌也不生气,依旧埋头吹他的笛子,他现在连在马背上嘴唇也不愿意离开那根笛子。
我们渐行渐高,天气越来越冷。
“这么冷的天,也许大家就不会得病了。
”罗鸿垂头丧气地说。
“那不是好事吗?” “因为来不及生病,大家就已经冻死了。
” 我们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队伍中没有现出任何人得病的征兆。
担当前卫的罗鸿或罗耷有时会带回一只兔子,或一连串雪鸡作为我们的晚餐。
如果运气不好,那我们也只能饿肚子。
仓佝这时候更害怕起我们来。
他根本就不要我们给他送的水和食物,每天蹲得离我们远远的自己弄,可怜他那么大个人,连火都不会烧,总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连胡子也燎掉了一大丛。
我们给他药草含在嘴里,他也扔了不要。
说起来真是造化弄人,一路上就他最小心,却是他终究先着了道儿。
那一天早上,仓佝自个儿去打水回来,我们发现他脸色苍白,眼睛里却冒着血红的鬼火,颧骨兀突而出,整个人的模样便如同死人一样。
“你怎么了?”我们问他说。
“我没事,我没事。
”他嘶哑着嗓子喊着说,“你们都别过来,别靠过来。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挨个瞧我们,我被他看得心里直发毛。
阿吉上前了一步想扶他,他猛地向后一闪,却因用力过大摔倒在地。
他扔了水壶,扶了树站起来,一只手上提着把不知哪儿摸出来的刀子,使劲地瞄着我们。
我一路上都没发觉他还有把刀子。
他开始说胡话:“你们都是强盗,”他疯狂地喊道,“你们想抢我的郡主,想抢我的珠宝,还有她,还有她。
都是我的,你们谁也别想抢走。
” “别靠近他,”向慕览冷冷地说,“他病了。
” 这句话好像彻底把他击垮了。
他大叫一声,跳起身来,想扑到郡主身边去。
我们此刻如何能让他再近郡主的身。
颜途一甩手,把剑柄朝前扔过去,重重地打在他的肩头上。
他踉跄了一下,捂住肩膀向后退去,然后突然转头跑开。
他披散着头发,一边跑一边号叫,那声音凄厉得如同夜枭的号哭,一层层地旋上天空,撞击到低沉的彤云才又重新落下来。
此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他。
“这是第一个。
”乌鸦嘴罗鸿低声说。
颜途连那柄剑也不要了,我们收拾起东西,那女孩还望着仓佝跑走的方向发呆,颜途招手吩咐大家上去拖了她,上马便行。
说实话能摆脱仓佝那个小人,我们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直到走出了半里多路,颜途突然醒悟过来:“那包金子呢?” 金子自然是被仓佝随身挎在腰上带走了。
我们火边的倾谈顿时都成一缕青烟飘走。
罗耷大怒道:“我去追他。
” 向慕览冷森森地说:“就算能赶上去,你敢去碰那些东西吗?” 罗耷不服气地道:“可是没了酬金,我们大家不都是白跑了吗?到底还走不走?” 我们一起看向那姑娘。
她低着头默不做声,看上去更加孤苦伶仃了。
她身体纤细,如果在展翅日的时候飞起来,那该是什么模样?她看上去也只十几岁模样,恐怕还没真正飞过呢。
“主顾没了,可是红货还在。
我们还是得将她送到地方。
”向慕览终于下了决心,“羽成容那家伙,也许愿意付钱。
” 此后,柳吉更是一步也不离开郡主了。
向慕览下了严令,除了柳吉,谁也不许靠近她。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孩什么话也不说,却似乎能和那小子的笛声交流。
柳吉吹的曲调我们谁也听不懂,反正都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调子。
只是每次听他吹起笛子时,她脸上的落寞神情便会少上那么几分。
看这笛子这么有用,我也努力地试着去听,果然慢慢地从笛子声里听出了一些东西。
我仿佛听到了天空中飘浮着一朵朵巨大的仙茏花,年轻的孩子们躲藏在花蕊中嬉笑,随后被带入高高的云端。
我仿佛见到了萤火虫编织成的花环,在深蓝的幕布上浮荡。
我看到了高大的年木上,那些漂亮的青年羽人环绕成圈,轻盈地向空中跳去。
那是皇族的飞翔。
他们多无忧无虑啊。
可是在这一切幻觉之中,透过晴朗的夜空,我依然能看到,南方的天空上正在慢慢升起一团大火,那是郁非,它跟随而至,仿佛厄运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死追不放。
越来越稀疏的植被提醒我们正在一天天靠近莽浮林的边缘,马上就走出了南药境了。
向慕览不时地回头后望,他什么也没看到。
没有任何跟踪的迹象,旷野和森林里都空寂无人。
只有厉风在空荡荡的谷地呼啸,将阴冷处的积雪卷起,猛烈地抛入空中。
这儿靠近鹰翔山脉,拐过死鹰岭后,我们就能看到巨大的缓慢流动的青色冰川了,那是宁州北部最著名的冰古河,它从鹰翔山脉深处蜿蜒而出,长达数百里,转而向东,最后终结在巨大的暴雪冰瀑处。
冠云堡就建立在暴雪冰瀑的对面。
冠云堡是一座冰城堡,完全用巨冰建成。
据说羽人的先祖建立了这座城堡,防备来自北方冰原的危险,所以这座城堡又被叫做“北方之眼”。
但北边只是一片蛮荒,裸露的群山不论春夏都被厚厚的冰覆盖着。
这么多年来,羽人们甚至不知道蕴藏在北面的危险究竟是什么。
生活在这片区域的羽人习性和生活习惯都与平地和山林里的羽人不同。
他们好像个子更高一些,毛发更淡一些,所以他们总自诩血统高贵。
此外,他们总围着毛皮衣服,厚厚的皮帽上插着羽毛,飞翔的技巧似乎也比平地上的羽人更高超。
“我们这儿离月亮近。
”他们总是这么吹牛,但不可否认,这帮冰原羽人有自己骄傲的资本。
对于青都来说,冠云堡并不那么听话,只是这里地处偏僻,气候苦寒,青都也就放任他们圈在这小小的一隅里骄傲去。
一翻过山鹰翔山脉到了北麓,密密的雪就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
在茶钥我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花,一片就有巴掌大。
路边的山崖上积满了厚厚的冰雪,稍有震动就簌簌抖动。
我们终于开始转而向下,道路极其狭窄,挂在悬崖边缘,脚下就是巨龙一样的冰川——晶莹闪亮的冰川裸露在我们脚下,表面上覆盖满了灰色的漂砾,裂缝有上百尺深,顶端微绿,底部则是深蓝色的。
马蹄在滑溜溜的山道上打着滑,而我们连人带马全都冻得发僵,但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浮现出笑脸来。
只要能走入冠云堡的领地,我们就安全了。
向慕览用鞭子指着前面说:“越过剪刀峡,路就不远了。
”大家相互对视,喜笑颜开,我活动了一下酸疼的脖子,却依然觉得头皮发紧,那种奇怪的紧张感并没有就此离开。
我们刚刚穿入那道陡峭的裂缝,就听到后面传来的轰隆声,如同上亿面巨鼓同时砸响,我们大惊失色地循声望去,鹰翔山发怒了,绝壁上的雪终于崩塌下来了。
无比巨大的雪浪瞬间从空中落下,腾起一路数十里高的白烟,十万白马奔跑的蹄声震撼大地。
这是决堤的白色洪水,和着数百万破碎的雪精灵的放歌,汹涌而下。
崩塌的地点离我们有十几里的距离,但山势陡峭,要不了一会儿工夫,那道白色潮水就势必会冲到我们这儿。
“向前跑,别回头。
”向慕览喊,用鞭子在我们的马屁股上猛抽。
我们身处的地方叫剪刀峡,两侧成排的尖利山壁相互交叉而列,如同一排剪刀架设在头顶。
峡谷尽头的石门只容许两人并排而过,石门上刻着一个狮子头,据说它的脸颊上有两道泪水的痕迹,所以也叫泪狮门。
越过石门后,地势骤然开阔,陡坡也变为缓坡,朝着宁北平原一泻而下。
如果被雪崩冲到峡谷里,我们一个也逃不了,全得被活埋在此,也许要上百年后才会被人挖出,但只要冲出石门,能逃到缓坡上,或者找个牢靠的遮挡物躲避,那就安全多了。
我们低头催马,向前猛跑,颠掉了行李,跑掉了蹄铁,甩掉了斗篷。
跑在最前面的罗耷斗篷被风卷走,蝙蝠一样飞起,正好罩在我的脸上。
我把斗篷从脸上抓下,一时眼花缭乱,只看见罗耷在快要冲入石门的时候猛烈地刹住坐骑,扭转身喊着什么,眼睛里露出恐惧的神色。
一根血淋淋的羽人矛猛地从他的胸膛里探了出来,把他架入空中。
马恐惧地嘶鸣着,在山道上滑动,然后撞在泪狮门上,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
紧随其后的我死命拉住马缰,几乎要把胳膊扭断,马儿拼命后仰着脖子,绷紧的肌肉在皮毛下扭动,但最后还是猛烈地撞到罗耷的坐骑上。
羽人矛带着哨音在空中舞动。
我向后翻滚,摔下马去,马翻过来把我压在下面,剧痛从腰里和大脑里生起,我翻了个身,躺在那动弹不得,看到后面伙伴们的马挤成一团,仿佛一只多足多头的怪兽。
“姓向的,我知道的近路可比你多啊。
”一个熟悉的嗓门放声大笑,崔虮子从泪狮门后走了出来,他招了招手,从石门后又涌出四五名弓手,站在两名长矛手的后面,张弓搭箭,闪闪寒光对准了窄路上的人。
“怎么样,你服输了?”崔虮子微笑着问。
他岔开双腿站在石头门前,虽然容光焕发,看上去却显得有些疲惫。
这些日子来他追赶我们也不省心省力。
他确实赢了。
此刻封住了我们前逃之路,而背后的崩雪正以万钧之势压下,我们无路可逃了。
“你,知道我们要去冠云堡?”向慕览问。
崔虮子把一颗黑糊糊的人头扔在我们脚下,头颅已经有点发黑了,但从三绺长须上勉强可以认出仓佝的模样。
“我们从狼嘴里抢下来的时候,就剩下这东西了。
当然,还有他的金子。
”崔虮子嘿嘿嘿地笑着,拍了拍腰间,得意之色滥于言表,“最开心的是,金子堆里还有封给羽成容的书信。
嘿嘿。
” “这位大人,”他用脚尖踢了踢仓佝的人头,“还真是帮了我不少忙啊。
” “现在,赏金、郡主,都是我的。
”他笑嘻嘻地强调说。
雪崩的锋面正急速朝剪刀峡猛扑过来,我们脚下整座大山都在微微颤抖,崔虮子却不着急,好整以暇地调侃着。
向慕览的黑马在滑溜溜的山道上率先站稳了脚。
他面色如铁,驱前两步,谁都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崔虮子也暗自戒备。
向慕览却突然一伸手,抓住了郡主的衣领,女孩轻轻地叫了一声,向慕览已经将她推出悬崖。
郡主半悬在空中,脚下一片虚空。
狂风卷来,使她的裙子在空中剧烈拍打,雪粒灌满她的头发,道旁一小块雪松动了,落了下去,悄无声息。
向慕览无情地将她向前推去,但她紧紧咬着牙一声不吭。
虽然呼啸而至的雪崩就在我们身后不远处,但山道上所有的目光在那一刻都望向向慕览,望向他手中那个无力挣扎的柔弱女子。
“崔虮子,你若不退开,我就把她推到悬崖下,你什么也得不到。
”向慕览喝道,声音里一点颤抖都没有。
崔虮子犹豫了一下,摸了摸自己的钩子,“不,你做不到。
”最后他说,死死地盯着向慕览的眼睛。
他们对视着。
雪崩的雷声远远传来,万钧雪浪如龙如熊,如狮如虎,排山倒海地呼啸而来。
我们都能闻到湿漉漉的血的气息。
罗耷的血,正顺着结了冰的山道流淌。
他还没有咽气,睁着一双发了灰的眼睛,挣扎着看向那女孩——我们豁出性命要送到冠云堡的东西。
余下的佣兵也紧盯着向慕览,只要他的手一松,我们就再无牵挂,可以朝泪狮门扑上去,和崔虮子决一死战。
我们全都红了眼睛,指望能杀一个是一个,但他们占据了不败之地,只要用长枪封住石门,乱箭射下,雪崩到来时往石门后一躲,什么事也不会有,而黑水团一脉,就此覆灭。
向慕览最终叹了口气。
他把手放了下来,把郡主轻轻放回到山路上。
小郡主身子颤抖,眼睛瞪得大大的,拳头捏得很紧,但依旧是什么话也不说。
向慕览宽慰似的拍了拍她的头,“我是做不到。
”他叹着气说,“你赢了。
把我的兄弟放了吧,要我怎么样都可以。
” 崔虮子放声大笑,“向慕览,过去在山里,你就一直压在我头上。
那时候我就想看到这一天,看到你跪在地上求我。
” “把女孩送上来吧,”他说,冷冰冰地横了我们一眼,“至于这些人嘛,把左手也都砍了,我就饶了他们。
” 他哈哈大笑,血从鼻子里流了出来,一滴滴地滴到铁钩子上,但他丝毫也没有察觉,只是仰着脖子大笑。
甚至他身边的士兵都发现了问题,静悄悄地向后退去。
他再低下头的时候,脸色已经全变了,黄中透蓝,眼圈下全是黑色。
罗鸿轻声但是清晰地说:“第二个。
” 呼啸的雪锋快速逼近,我们甚至看得出那些雪雾中隐藏的形象,那是成千上万的大象、成千上万的雪狮、成千上万的白熊、成千上万的白龙,它们冲撞着大地,天地摇撼,长长的冰川呼啸着,呻吟着,长长的冰蓝裂缝张开又合上。
一名羽人长矛手突然转身,开始没命地逃跑。
接着所有的士兵都开始掉头逃跑了,他们奔跑的时候,又有一个羽人咕咚一声一头栽倒在路上,一动不动了。
“第三个。
”罗鸿数着说。
我勉强支撑着,从马鞍下抽出笨重的身子,站了起来,正好扶住摇摇欲坠的郡主。
巨响犹如霹雳,雪已经扑入了峡谷,冰块如雷而下,宛如庞然巨兽的咆哮,它们一瞬间的工夫就涌过了长长的通道,扑到了身后。
向慕览冷冷地说:“跳。
” 凶猛的雪兽猛撞在我们背上。
冰和雪的舞蹈。
仿佛展翅日到来,我们腾入空中,又翻滚而下。
飞泻的冰雪从头冲下,遮天蔽日,盖住了一切。
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闻不见。
成千上万的军队和铁骑暴雨般驰过头顶,狂暴的铁蹄踏过我的颅骨,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紧抓住女孩的手,飞腾,坠落,翻滚,良久才落地,嘴里灌满了冰泥。
石头狮子门好像一道屏障,它把我们遮蔽在落满泪痕的石块后,那儿充满了幽暗、泥土、水流和生命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亲吻大地,哭泣出声。
飞扬的旗帜从云端里探出,展露出一颗银色骷髅,头上围绕着一条咬着尾巴的蛇。
那是凛北王的旗帜。
它们迎风招展,如同一群苍鹰翱翔展翅。
冠云堡就在对面。
朦胧的白雾散开了,厚实的冰墙后矗立起无数重重叠叠的冰尖顶,就像冰川下的冰塔林。
每一座塔楼都雕满镂空的窗花。
阳光从缝里钻出来,就好像点亮无数缀满钻石的风车。
它们并不都是白色的,有浅绿、淡蓝和更深邃的古蓝色。
那都是冰本身的颜色。
阳光玩味着它,摆弄着它,折射出七彩的光。
这是座仿佛用水晶雕刻出来的城堡,像是公主案头的玩具,却怎么也不像用来防御强敌的堡垒。
“难怪冰川羽人如此骄傲。
”罗鸿使劲地抬着头看那些旗帜,“他们看不上这瘦姑娘,我们要不到好价钱的。
” 那时候我们正站在冠云山对面的一处屯兵哨所里,巨大得不可思议的冰瀑直挺挺地从我们脚下的山崖裂口俯冲而下,直冲数十里外的冰原。
冠云山那高耸的冰峰插入云中,尖削如刀,只在肩部有一处隐约的缓坡。
那座冰城堡就修筑在那里。
我们六个人都奇迹般地都从雪崩中幸存了下来,只是失去了所有的马。
我和那女孩花了三个时辰,陆续从雪坑里挖出了向慕览、颜途、罗鸿和柳吉,然后是罗耷的马。
我们怎么也找不到罗耷的尸体了,所以我把他的马鞍解下,扛在肩膀上走了一路。
在屯兵所,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郡主身上那块佩玉解下,让哨长送到城堡去。
那块王家佩玉的效力果然很大,冠云堡人给了我们从未有过的殊荣——凛北王要亲自来哨所迎接郡主。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队骑兵,正从冠云山的冰坡上俯冲下来。
他们行走得比我们预计的要缓慢得多。
距离还很远,也只有羽人的眼睛能看出来——队伍中有一辆庞大的马车,虽然拉车的八匹马奋力奔跑,但还是拖累了骑兵的速度。
直到天快黑时,铁骑护卫队喧闹嘈杂的蹄声才真正宣告了凛北王的到来。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明明是生活技能,你却练成神技写写写写写写写
- 太乙雾外江山
- 每次暗杀仙君都失败[穿书]闪灵
- 温柔的某某某Fuiwen
- 19世纪女继承人三春景
- 即刻热恋依存体质
- 绿茶徒弟偏执又疯狂醉折桃花
- 嘘,我其实知道他是谁一江听月
- 神级工业主五彩贝壳
- 人道天堂荆柯守
- 我靠开医馆闻名全世界盼星星
- 伊尔塔特的农场秋野姜
- 黑豹传奇戊戟
- 剑道之王乘风御剑
- 穿成一只话痨鹦鹉我爆红了江湖不见
- 逍行纪血红
- 我在咒术界当文豪东山高卧
- 九龙圣尊莫知君
- 被写进柯学漫画的我扭转了命运沐裕鹿
- 有生活系统后我暴富了安宫的竹子
- 龙族:从只狼归来的路明非火龙果大亨
- 亡国后捡到了当朝太上皇一捧秋凉
- 传闻余酲
- 纸婚惘若
- 证道天途寂灭前尘
- 从修真界回来后我红了剑鸣如歌
- 纪律准则顾言
- 涟漪效应时星草
- 才不要当万人迷O君水益
- 幸存者偏差[无限]稚楚
- 黑巫师朱鹏狂翻的咸鱼2
- 请不要给工具人加戏[快穿]洛云九
- 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春山木
- 我是一个原始人墨守白
- 横刀城郭如旧
- 重生我对感情没有兴趣纯纯不失眠
- 造化之王猪三不
- 在柯学世界当小学生魑归
- 科举文里做考官辛宸
- 皇后她不干了深碧色
- 人道天堂荆柯守
- 阴阳渡梦溪石
- 全物种变异后我开了挂千灯黄酒
- 武侠之神级捕快紫衣居士
- 青玄道主中原五百
- 刀破苍穹何无恨
- 复唐寻香帅
- 别那么野顾子行
- 汹潮林汀汀汀汀汀
- 被穿越者夺舍以后青花燃
- 美恐副本自救攻略墨兔儿
- 万古神帝飞天鱼
- 垂涎弄简小号
- 甜蜜一生陈之遥
- 这个诡异三国游戏太凶残了月下藏锋
- 荒岛求生,开局三倍宝箱翩翩晚照
- 太平令阎ZK
- 盗墓:我,陈玉楼,一心修仙超自然的猫
- 娘娘福星高照[清穿]岳月
- 贵妃吐槽日常(清穿)玄北
- 奴隶养成后,她们都翻身做主了ccc
- 总被召唤的我于高危世界成为大佬申屠此非
- 剑仙裴牧云步帘衣
- 炮灰夫妇今天也想暴富臣音
- 师姐空有无边美貌赏饭罚饿
- 有钱算特长吗八月糯米糍
- 陛下今天火葬场了吗/无情眼杳杳云瑟
- 师祖为何还不飞升海盐芝士卷
- 错嫁年代文大佬后[穿书]雪耶
- 华枝春怀愫
- 前男友成为首富后乌龙煮雪
- 伊尔塔特的农场秋野姜
- 周末惯例别四为
- 西域列王纪(四方馆原著小说)陈渐
- 男主怀了我的崽顾西子
- 亡国后捡到了当朝太上皇一捧秋凉
- 夏日撞上南墙甜舔
- 垂涎弄简小号
- 壮汉老实受被豪门大佬独宠了木万千
- 五零香江豪门生存法则老衲吃素
- 甜蜜一生陈之遥
- 八零香江大美人刺棠
- (综历史同人)[秦]想当国师的我却成了太子青鸟临星
- 随军年代文二代躺平日常[六零]最近爱吃酸辣粉
- 这个诡异三国游戏太凶残了月下藏锋
- 太平令阎ZK
- 社恐被迫秀恩爱[快穿]春山木
- 奴隶养成后,她们都翻身做主了ccc
- 异世海商魔法少女兔英俊
- 进京赶考还分配老公吗?长鼻子狗
- 被迫奉子成婚之后云闲风轻
- 闻妻有两意忘还生
- 小丧尸NPC的养成日记月见茶
- 华枝春怀愫
- 一个雨天殊娓
- 我的超能力每周刷新一片雪饼
- 伊尔塔特的农场秋野姜
- 周末惯例别四为
- 路人她超神了龙柒
- 认真躺平,佛系宫斗长翘